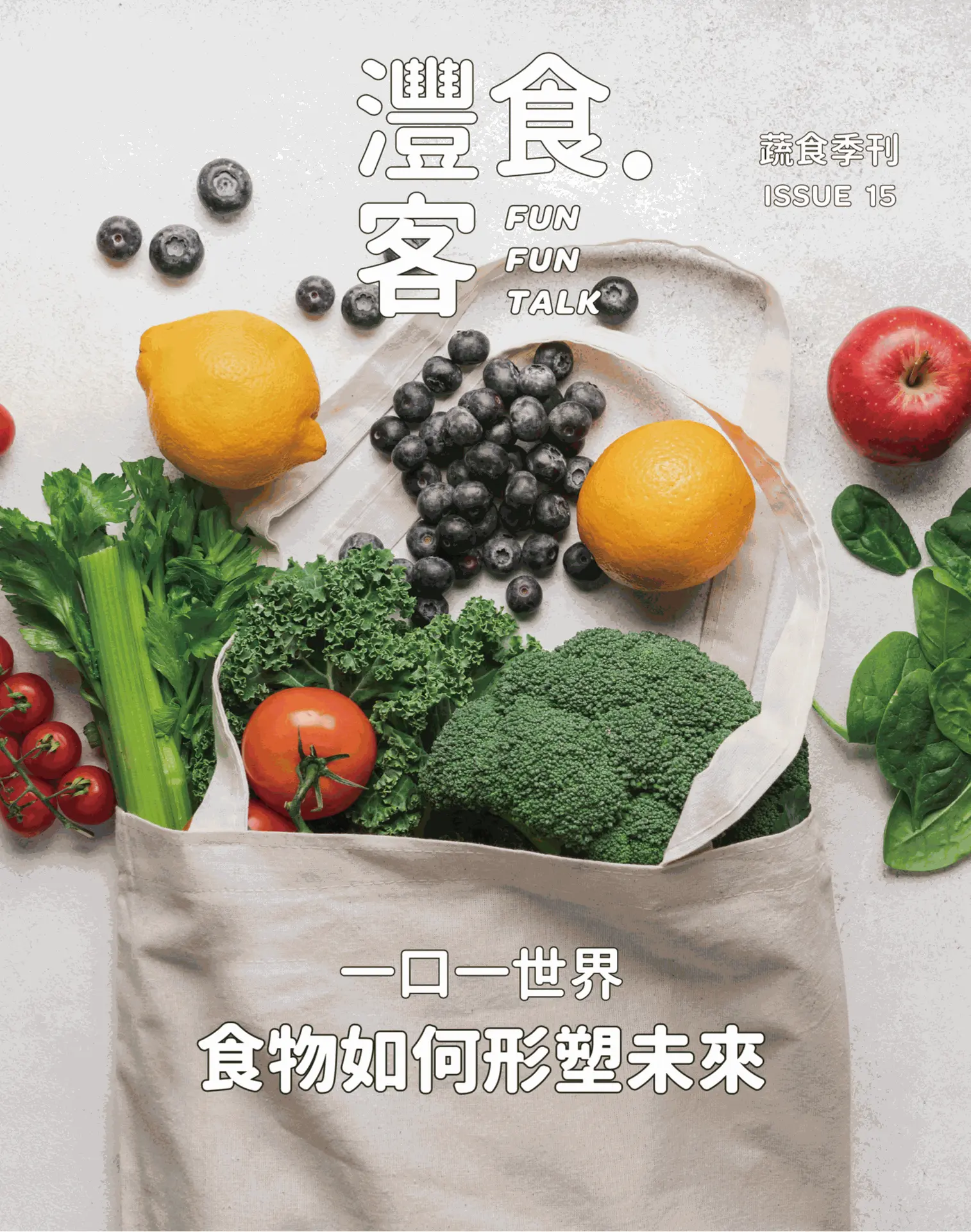小時候,阿嬤帶著我搭當時的北淡線到淡水,走在重建街的階梯街道,旁邊有很大的石頭。老家對面就是一間雜貨店,親戚很客氣的到雜貨店拿了一大堆汽水跟冰淇淋給我吃,讓我對這兩個食物產生記憶連結,所以後來就覺得,淡水是個有香味的地方......
圖片來源:淡水香草街屋 提供

從屋頂盆栽開始的香草夢
本來是媒體工作者的蔡以倫,十多年前開始研究香草,並在阿嬤淡水重建街上的老房子成立「香草街屋」,從事香草種植跟推廣工作,透過茶飲跟課程讓大家認識不同的香草植物,也學習如何把香草運用在生活中。
蔡以倫的香草旅程始於十多年前,當時啟發他的,是在淡水經營中藥行的叔公。有一次,他看見叔公用仙草、甜菊加上薄荷慢火熬煮四小時,竟然做出沁涼甘甜的仙草茶,這讓他大開眼界。「原來天然食材也會有如此有層次的味道。」那時起,埋下他日後投身香草茶製作的種子。
「我是一個都市長大的小孩,以前根本沒有種活過什麼植物的經驗。」他回憶當初在淡水重建街老家透天公寓屋頂上,試著種起香草盆栽。原本只是想把這空間作為教學用途,沒想到竟種出了心得,也逐漸引來朋友的鼓勵與關注,促使他擴大規模,成立「香草街屋」。
從最初種植開始,一步步拓展到配方研發、烘乾處理、包裝設計等,甚至開發自有品牌商品。40歲那年,他敏銳感受到人們渴望天然保健食材,於是辭去媒體工作,回到淡水老家,在下圭柔山的香草園裡重新出發,並開始向親戚請益,透過嘗試累積實務經驗。由於香草具有強烈季節性,也並非每種都適合臺灣氣候,他試種了兩、三百種不同香草後,才逐步篩選出真正適合當地環境、同時容易照顧的品項,作為商品開發的核心。

寫香草,也寫臺灣的味道與記憶
投身香草種植後,蔡以倫也接受過去媒體同事的邀請,在報紙上開啟〈香草隨食札記〉專欄。撰寫內容包括介紹臺灣人常種的香草,也傳授大家如何種植的小祕訣,寫稿時,始終堅持先拍照、實地觀察後再動筆,不憑空描寫那些在臺灣難以存活的「歐洲名草」。當常見香草寫得差不多後,他開始介紹起青草與野草,像是藥用價值極高的車前草,勤於筆耕的他,如今已累積逾百篇的專文。
講到香草,閃過腦海大部分會說出像是薰衣草、百里香這些生長在地中海地區的植物;但對蔡以倫來說,倘若把「香草」定義成,有香味、帶有一點療效的植物,那其實全世界應該都有,因此,不應該被受限在地域,其實臺灣也有原生植物,例如臺灣早期就落腳的「黃荊」,便兼具保養與驅蟲功能,只是知名度不高,需要更多解說與推廣。
談到推薦的香草植物,他首推「檸檬香蜂草」(Lemon Balm),遠遠看像薄荷,在臺灣算常見,但大眾卻不是很認識它,甚至有些花市老闆會把它介紹成檸檬薄荷,但其實它不涼。檸檬香蜂草是檸檬味,而且泡起來居然有蜂蜜味,也可以幫助安神,「所以我覺得,檸檬香蜂草是臺灣可以種、味道、效果又好的香草植物。」
香草入生活:從盆栽到茶杯
蔡以倫也不吝分享種植經驗。倘若把香草種在陽臺上,要換大盆、增加土壤量、提高保水力,是提高香草植物存活率的關鍵。如果空間跟採光不足的話,他則推薦可以選擇「到手香」,這種植物即使兩週沒澆水也不易枯死,雖不可食用,但對蚊蟲叮咬有急救效果。
他強調,香草植物其實不太需要水,基本原則就是「寧乾、勿太濕」。什麼時候該澆水?蔡以倫說可以拿起花盆去感受重量,「如果覺得好輕,輕到你感覺裡面是不是沒水?但其實這個時候對香草植物來說還是ok的;如果拿起花盆卻明顯感受到水的重量,那就要警覺,不能長期讓盆子這麼重,水量過多了,這時候就不能太愛它!」
而最受歡迎的香草商品,蔡以倫說,這就非「洋甘菊」莫屬。「淡水很適合種洋甘菊,後半年氣候轉涼剛好。開花時,滿園充滿蘋果香氣,收成後,再與紫蘇、甜菊混合製成茶包。」他指出,不管是中醫或是香草領域,很多人都是因為情緒或是睡不著接觸洋甘菊,所以洋甘菊是全世界最熱銷的安神用茶。「但茶是慢慢喝的,不要期待一壺茶,就能立刻解決失眠問題。」
至於「香椿」,則是他多次挑戰失敗的植物。這種植物雖有益健康,卻因味道強烈讓消費者卻步,「我嘗試使用很多香草去壓它的風味,但市場上好像只要看到香椿兩個字,就會抗拒消費,因為大家普遍認為它是食物不是茶,但其實,它擁有很不錯的效果。」除將不同香草植物組合外,後來他還加入果乾,藉此提升口感與價值。「柑橘、蘋果類,是大家普遍都接受的味道,而香草本身少有柑橘味,加上果乾後,不但質感提升,價位也更有空間。」

認識香草:讓味覺有更多選擇可能
除了經營香草街屋,蔡以倫也透過社區大學與受邀講座推廣香草文化。他將香草植物融入在DIY課程中,引導學生理解比例與屬性,讓學習更立體有感。例如以檸檬草、檸檬香蜂草、芳香萬壽菊、甜菊混合泡茶,分別可以創造出檸檬、檸檬加蜂蜜味、百香果與甘甜的層次風味,「如果我把常見的香草全部唸過一輪,大概有些人已經呈現昏迷狀態了!」蔡以倫說。
對象若是小學生,他會強調「食物,可以自己種」這個觀念。他提到,孩子喜歡喝的飲料,裡面可能有糖、色素,還有很多不自然的東西,但只要學會種香草,認識不同香草植物的組合,大家都可以泡出顏色好看、味道好喝、甜度適中,對身體較無負擔的飲品,「其實孩子都知道該怎麼吃喝,雖然大人告訴他們要少喝含糖飲料,但好像沒有什麼替代品,所以只要把香草調成適當的組合,告訴他們可以喝天然食物的飲品,還能將這些概念傳達給家人。」
蔡以倫談到,種植課程在都市學校最常會遇到的問題,就是大部分家庭不論是時間或空間上都不太適合,不過他觀察到,許多校園建築其實蠻空曠,例如走廊外的女兒牆就可吊掛植物,因此,只要善用空間,「孩子其實可以把植物留在學校照顧,這也是一種延伸教育。」
「味覺是根深蒂固的文化,但大家要知道的是,其實我們有更多選擇。」蔡以倫說,現在熟悉的香草,大多來自地中海沿岸地區,早年在當地,它們不只是調味料,更肩負著治病與保存食物的實用功能,隨著時間推移,才逐漸演變為西方料理中不可或缺的味覺元素;就像臺灣的飲食文化,幾代傳承下來,以蔥、薑、蒜、胡椒等來調味看似平常,但其實很少會用鼠尾草來醃製食物,也不太會拿香茅來替代薑。
「想要告訴大家的是,其實別的國家的做法,如果有好處,是可以學習的。這不是要你改變計有的飲食習慣,而是讓食物的來源和選擇變得更多元。」他舉例,臺灣人吃麵線時若沒有放九層塔或香菜,可能就會覺得「哪裡怪怪的」;但在西方飲食文化裡,香草的搭配往往更自由,不一定有固定組合,重點是能給人更多選擇的空間。
香草街屋的空間雖小,但蘊含著豐富的知識與經驗。蔡以倫用香草種植打開了一條從飲食連結到土地與社區的道路,讓香草不只是茶包裡的風味,更是文化裡,不可或缺的日常香氣。